您现在的位置是:主页 > 野史趣闻 > 野史趣闻
曲林东正史野史杂谈 文史知识
![]() admin2023-11-22【中国历史故事】人已围观
admin2023-11-22【中国历史故事】人已围观
简介进入 正史与野史杂谈 正史和野史是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两种史料。 千百年来,学者们对于正史和野史的含义以及各自在史料中的价值有着不同的看法。 正确认识上述问题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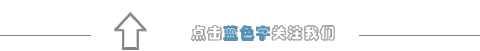
进入
正史与野史杂谈

正史和野史是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两种史料。 千百年来,学者们对于正史和野史的含义以及各自在史料中的价值有着不同的看法。 正确认识上述问题关系到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对当前历史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
正史与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出现,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达的时候出现的。 金玉甫先生认为:“正史之名,唯有《隋志》”。 新编《辞海》(1979年版)说:“梁阮孝绪有《正史伐扇》,正史之名《隋志》成书于七世纪中叶,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阮孝胥(479—536年)是公元五世纪之交的人。及六世纪。》早了一百二十、三十年。可惜阮书已失传,所以现在只能从《隋志》来讨论正史的意义。
《隋书·经纪志》是史部第一部正史类,其序曰:“古之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言行记载,后世事多,道繁复……,皆仿禁马。昔正史,由右光所著,一代史数十部。” 可见,《隋书》中所谓正史,是指《史记》、《汉书》等传记史书。 除传记体的历史外,还包括对这些史书的注释、解释、语音训练、音义、批驳等作品。 刘知几写了《史通》,尤其是《古今正史》一章,但其所谓正史的意义与《隋志》有很大不同。 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的结尾写道:“大概是自古史家所写,大纲是这样的。字是用来比较事物的,月是年。是的。”历史事件的基础,并充当陌生人的眼睛和耳朵。” 那些写他们的人都在这里。 自从于片基的小说之后,我就没有时间讨论它们了。” 在这里,刘知几把自古以来所有“史家所著”的书籍都视为“正史”。 因此,从先秦时期的《尚书》、《春秋》到唐初的正史,无论纪年、传记,都在“古今正史”的范围之内。 他的正史的意义比隋志要广泛得多。 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意义,对后世许多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旧唐书·经记志》继承了《隋志》的风格,也是史部第一部正史,“以志录为记”。 《新唐书·易文治》、《宋史·易文治》皆因于此。 清代中叶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 其《史部总目》曰:“今群书,分十五类。第一正史,纲目也。” 《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十之七定于宋。 明代监修本,合宋、辽、金、元四史,共二十一篇。 皇帝命《明史》,又赵曾《旧唐书》二十比三。 近已收四库,薛居正《五朝旧史》已编撰。 与欧阳修的书并列,共二十比四。 现在是官方学校记录的。 评经典者,不会乱发表。 覆正史,配经义,非悬诸令,不敢私增。 其故与稗官、野史不同。”将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审则不乱刊”、“若有”。不为停令,私不敢加”,使正史在史书中处于最高地位。与正史相关的著作,如解释音义、整理等查漏补缺、辨别异同、纠正字句,都列在每部历史之后。从此,两百多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仍为人们所使用。
与上述传统认识存在较多差异。 是清代雍、干年间定稿出版的《明史》。 史前记载古今书籍,以为皆在时代之柱下。 明万历年间,焦洪编修国史,编有《经籍志》,堪称详实。 看看前辈陈编的,何必靠记载呢? 只是捡起遗物,希望能传承《岁志》,但假书却错误列出,这就是错误的。 因此,当前章节大约是270年的著作,一点点可以分为一录。”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列出的书籍都是最近270年的著作。年代,内容多为宋元明历史事件,体例有传记体、纪年体、纪事体,这明显受到《古今正史》和《书志》篇章的影响近代历史学家华冈曾给“正史”下过定义,其意义与刘知几的理论颇为相似,他在《中国历史的逆转》一书中写道:“所谓正史”正史是历代皇帝都认可的一大套合法的正史,而从唐朝到清朝期间形成的正史都是由皇帝指定的史官编撰的。”
以上两种对正史的理解是指传记国史和正史书。 前者的内涵较为具体,而后者的内涵则过于宽泛。 我鄙视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史”、“野史”,不过是沿用了历史上的惯用术语。 我主张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应该区分上述两个“正史”概念:一般情况下,正史书可以称为正史;一般情况下,正史书可以称为正史;一般情况下,正史书可以称为正史;一般情况下,正史书可以称为正史。 “一般标题”是合适的。
二
野史的出现不仅补充了正史,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的内容。
“野史”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 鲁龟蒙有诗云:“自爱名扬野史”(《赏击美人见苦雨》)。 卢龟蒙(?—881年),晚唐人,弃官隐居,在松江富里耕作,孜孜不倦地著述。 应该说,这样的“隐君子”写出“自爱闻名于野史”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吕龟蒙看来,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入“正史”,而他这个“姜尚岳父”则认为进入“野史”是高贵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野史和正史是有很大不同的。 史料记载:“(唐昭宗)《龙记》中,有学者沙仲穆编纂野史十卷,起于大和,止于龙记。,《策夫元贵·国史部·集撰二》” )沙仲牧与吕桂蒙大致是同一代人,这可能是我们所知的第一部以“野史”命名的野史著作,宋代以后,以野史命名的著作逐渐越来越多。例如,北宋的龙衮着有《江南野史》,记述南唐历史事件;“类记《野火编》八卷,《野火编》十一卷”。 《夜安夜朝》、《三朝野志》七卷、《夜集孟搜》十二卷、《南诏野史》一卷。 有《南明野史》、《清朝野史》等。 事实上,那些被称为野史家的人,只是野史家中极小的一部分,真正的野史家数量远不止于此。 宋代左珪编的《百川学海》、元代陶宗仪编的《说语》、清代学者流云编的《明代稗稗史》等书,近人编撰的《清野史大观》,收藏了丰富的书籍。 非官方历史数据。
从野史的起源来看,它原本是杂史的一部分。 唐代沙仲牧所著的《大和野史》和《新唐书·艺文志》均属“杂史”类记载。 明代齐承顺所著的《丹生堂藏书目录》,分为野史、稗史、“杂史”类中的杂记三类。 这一切都证明野史实际上是来自于杂史。 《隋书经记志》史部“杂史”跋从文体、作者、内容等方面概述了杂史的几个特点。 从体例上看,西汉以来,有些史书“属言物,与《春秋》、《史记》、《汉书》不同。 1、从体裁来看笔者认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家失去了平常的守护。 诸菩萨诸学者,皆废,皆记录所闻所见,以备其死。 为后人所景仰,作者众多。 ”,这是第二;从记载的内容来看,东汉以后,史学逐渐突破官府的藩篱,发展到民间,所以“士人集旧史甚多,成书”。他们自己的。 它以雄心勃勃而闻名,但制度却并不与时俱进。 还有委里之说,怪诞荒唐,真假莫测。”这是第三种。杂史的这些特点,使其与正史有明确的界限和差异,也可以可以说是其“野”的表现。“杂”与“野”是相关的。刘知几的《史通·杂言》列出了正史以外的十种“史史六别”:旁注、小记、轶事、琐事、县书、家史、传记、杂记、地理书籍,城市薄薄,其中不少属于野史范畴。
宋明以来,野史得到发展。 嘉靖十九年,明高儒着有《百川书志》。 野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所谓“野史”的内涵也越来越广。 宋代洪迈在讨论野史时以沈括的《梦溪笔谈》为例,而元修的《宋史》则将《梦溪笔谈》列入《艺文志》的“小说”范畴,清修的《四库全书》则将《梦溪笔谈》列入《艺文志》的“小说”范畴。它包含在细分中的“杂项住户”类别中。 如上所述,《宋史·艺文志》中将《新野史》归入“传”范畴,而《野史甘露记》、《大和野史》则归于“传”范畴。 可见,宋元以来,“野史”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近代,梁启超开始明确将其他历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称为野史。 这是史学界首次对“野史”的内涵做出更为精确的规定。 近代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认为:“凡是文人、文人、文人、穷学者所写的史记,凡非正史记载,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或杂学者”。 (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概述》,《史料》1980年第5期)这种说法可以与上面引述的华冈对“正史”的定义进行比较。
一般来说,对于野史的内涵有两种理解:谢国桢的《野史笔记·百成杂家》是指广义的野史; 梁启超所谓的单史、杂史、杂传、杂记统称为野史,是狭义的野史。 前者易于人们理解,而后者则内涵更为精确。 每个都有自己的优点。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用谢国桢的理论,具体情况应该遵循梁启超的理论。
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后,学者们常把野史称为稗史。 例如,明朝商君编印的《稗海》一书,收集了历代野史杂记七十余种。 清代居士刘云编着《明代稗史》一书,共编撰了野史笔记等16种,把野史称为稗史,其实是不正确的。 《稗史》的理论源自《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是从稗官流出来的,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人所创造的”。 颜师古注引春曰:“谈街巷,皆于细节。 王欲知街巷风俗,故任稗官为使者,以谈论之。” 不过,师古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并接着注释道:“稗官是小官。”《汉代名臣》唐琳请省任官,大臣、官员、稗官各减少了十三个,没错。” 由于人们忽视了古代注释,将稗官等同于小说,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错误。 于家熙先生在《小说家出自稗官》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一点,并指出:“子如春误将稗官当小事,《汉志》所记载的书籍已绝迹,后人看不到。古代小说的体裁,就是所有小书,包括杂史记,都叫稗官野史,或者稗官小说,或者稗官世家。” (《于家熙论学杂着》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278页)把所有琐碎的书都称为“仓官小说”,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尤其不宜称其为“谷仓正史”或“谷仓史”,然后用谷仓史来泛指野史,这是特别不恰当的。 前文提到,稗官原本是一个小官,他的任务就是采访大街小巷的风土人情和民间琐事,所以小说家由此受到启发。 如果记载的内容可能与历史事件有关,那么后人称其为稗史,也多少有些道理; 如果仅凭记载就称为稗史,甚至用稗史来囊括野史,显然是不恰当的。 因为:按照《汉书》的本义,稗官所记载的记录是“街谈巷闻”,但野史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此,比前者要广泛得多。 清代潘永殷的《宋白雷朝》和近代徐克的《清白雷朝》,似乎把杂记琐事的史书视为白史更为恰当。
三
从史料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问题是,这里的重要性和优先级之间有区别吗?
《隋书·经记志》将正史列为史部之首,可见其对正史的尊重。 他在《杂史》中说:“然而,多为帝王之事。君子知人,必博览群书,判断要点,故备而存”。 这里说的是“广泛收集,广泛阅读,判断要点”。 《奇要》不主张对杂史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这是很有道理的。 刘知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隋之更清楚。 他在《史通·杂书》中主张《杂书》史中“择善从之”是正确的。 我想这些意见可以作为我们对待野史态度的参考。
《隋志》和《史通》中的上述观点也符合野史的实际情况。 虽然野史笔记的作者常说是为了助他们谈笑风生,安度晚年,但事实上,正如唐朝李昭在《国史补》中所写的那样,就是“考虑家族的历史或者弥补家族的不足”。 正因为如此,在历史史上,从唐宋到明清,野史笔记受到了许多著名史学家的重视。 甚至有人认为,野史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正史的编纂。 清代赵昭在评金元史时说:“自古以来,稗草的记载,不比两宋多。《门录新语》、《碧螺录》虽不诽谤正义者,一代文献得以保存,学者研究其历史,可以帮助正史。史学家赖以编撰的《龟田录》和《中州集》;元朝只有《追耕录》这本书,其中含有许多淫秽词语,所以宋(廉)、王(洪)诸侯都有使用平板电脑上的文字、行为和其他词语,这些东西非常漂亮。” (《猇亭杂录》卷二《金元史》篇)。 昭仪认为,很多野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来源之一,这是好的。
近年来,刘野秋所著的《历代笔记概览》(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一书,对两类历史轶事和考证的史料价值做了很好的分析。辩证法,认为对于研究一代人的史实、典籍、记载有重要意义。 它是轶事风俗不可缺少的资料,因为“从史料来看,历代笔记中许多具体详细的记载,往往是正史书上找不到的,足以帮助我们弄清楚真相。” ” 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50、60年来出现了过度抬高非官方史料价值、过度贬低官方史料价值的倾向,应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 1922年,梁启超撰写了《中国史研究方法》。 他还列举了几个历史例子来帮助说明这一点。 梁对视觉历史史料的重视当然是正确的。 但他对野史的推崇太高,以至于认为“无名之人所写的半通笔记”可与《史记》、《汉书》相媲美,“等人之耻”之说是不合理的。 ”。
1945年,简伯赞先生在《略论中国文字学史料》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这一观点:“就史料价值而言,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其他历史”。 ,而正史以外的其他历史,都不如史记。还有其他的文学群。” (《史料与史学》,国际文化社,1946年,第8页)简老对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他的上述结论并不正确。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应该把一切文献都视为史料; 但如果他们认为史书不如其他书可靠,正史不如野史重要,这就是本末倒置,混淆轻重。 大约与简老写上述文章的同时期,华纲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的翻转》一书中讨论“正史与野史”,也有类似的倾向。 我认为谢国桢先生在《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对“正史”的看法值得进一步探讨。 谢说:“我觉得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官员们编撰的‘正史’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除了记录皇规、帝王将相、宰相严明、政治官场兴衰、社会经济形势、朝野遗产、劳动人民创造的事迹历史和创造的财富都非常少。” 尽管《二十四史》有种种局限性(如阶级局限性、史料局限性等),但将其视为近乎谎言的骗局,似乎有点简单化了。 既然历史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那么它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 当今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新研究一切历史”,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去其糟粕,“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如果简单地宣称以往的史书(尤其是正史,或者“二十四史”)“不真实”、“不可靠”、接近“谎言”等,历史学家将很难完成上述内容任务; 因为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野史,或者主要依靠野史来恢复历史的面貌。
如何理解正史和野史在史学上的价值? 笔者认为,正史仍然是我们了解一代人历史的主要材料,而野史则具有填补、丰富和纠正正史错误的作用; 有了前者,后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而后者的存在将使前者更加完整。 这里必须澄清两个问题:
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历史著作,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不能为人民写历史,也不能写人民的历史。 《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在古代史书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虽然不能代表司马迁全部的历史政治观点,但仍然难免受到后人(包括刘知几这样的伟大历史学家)的批评。 野史注记中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和诽谤,未必会载入正史。 当然,由于野史笔记大多是“反对派”文人写的,对当时统治集团的保护和禁忌可能较少,书写也比较直白。 但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野史可靠,正史不可靠。 对于旧历史来说,“可靠”和“不可靠”是相对而言的。 从国家历史,或者某个朝代的历史来看,也就是从整体来看,正史应该比野史更“可靠”,因为野史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而只是反映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的一角。 相反,当谈到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某个人时,正史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清楚。 野史的杂记非常详细,因此比正史更加“可靠”。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对待历史遗产(包括历史遗产)时,应该予以批判性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而不是强调在某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遗产,它不恰当地贬低了遗产另一方面的历史价值。 两百多年来,不少论者对唐五朝以后编撰的正史书提出过批评。 看来,正史书已经成为史学发展的一根刺了。 然而,官方修史书为何不废止呢? 统治集团需要控制史书的编纂,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客观原因(如文献越来越多、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 我认为这需要认真研究。 另外,后朝为前朝修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 我们不应该以“官修史书”为由轻易抹杀这一优良传统。
四
一些评论家在评价正史和野史的价值时,或者在抬高野史的地位而贬低正史的地位时,常常引用鲁迅《华改记突发思想》中的一段话:“中华之魂”。历史上写着,预示着未来的命运,但因为画得太厚,废话太多,很难探知其中的细节……不过如果看看野史和杂记,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毕竟他们不必表现得像历史学家……” 毫无疑问,鲁迅的话是深刻而正确的。 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些论者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依据和证据。 依笔者拙见,鲁迅的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
首先,应注意视觉历史和杂记。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谈到野史的重要性。 他认为非官方的记录更加直白,不会摆出历史学家的架子。 “可以更清晰地看待过去的事件”,更深入地揭示社会。 非官方历史是由私人撰写的。 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个人恩怨和恩怨”。 这也是无法写下事实的原因之一。 不过,一般来说,并不过分。 但鲁迅主张读宋明史,不能仅仅看成是讲历史,而主要是讲政治和现实。 根本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历史的教训。 因此,我们在理解鲁迅的上述论断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条件,更不能忽视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其次,鲁迅并不否认正史的重要性。 这一点常常被一些崇尚野史、贬低正史的评论者所忽视。 Just before the quotation from "Hua Gai Ji Sudden Thought" quoted above, Lu Xun also wrote: "Previously, I heard that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are just a 'Xiang Ke Shu', a 'family tree of a single husband', etc. I thought it was true. Later I looked at it and understood, why is it so?" This shows that Lu Xun's views on official history also have a development process. After reading history and thinking on his own, he changed his simple views such as "Xiangqi Shu" and wrote these crucial words: "The soul of China is written in history, indicating its future destiny." As Lu Xun got older,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official history. In August 1932, he wrote in his letter "To Tai Jinnong": "I had wanted to read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and I had requested a volume from the Commercial Press. However, this year it had to be postponed until the winter of the year after next. , only taking cod liver oil can prolong life but keep the disease at bay." As a writer, thinker and revolutionary, Lu Xun's profound vision and keen thinking were also helpful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history.
Third, Lu Xun's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official history is indeed very clever. According to Lu Xun, history "writes the soul of China and indicates its future destiny". If people can erase the thick "paint" and eliminate the layers of "nonsense", they can "see It comes from the "truth" of "soul" and "future".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Lu Xun saw on the one hand the "genealogy of emperors and general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glory of the "backbone of China". Lu Xun's serious critical spirit in treating historical heritage, as well as his pragmatic attitude of strictl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irty water" and "children", are worthy of our study. It is inappropriate to cite only one passage of Mr. Lu Xun as evidence to exalt unofficial history and belittle official history.
——This article is excerpted from "My Historical Life" by Qu Lindong,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November 2016, priced at 39 yuan
Long press fingerprint
One click purchas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for this magazine. 2017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will continue to accompany you closely.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when you are busy:
1. Go to the post office to order, post code 2-271.
2. Remit money to the magazine through the post office to subscribe to new issues and some old issues. Mail order addres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magazine, No. 38, Taipingqiao Xili,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Postcode: 100073), Tel: 63458229. When remittance, please clearly indicate the number, quantity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purchase. 10% of the total price will be charged for postage. If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an additional 3 yuan registration fee will be added.
3. Readers in Beijing can go to Sanlian Taofen Bookstore, All Saints Bookstore, and Bohong Bookstore to buy, or go directly to the magazine (No. 38, Taipingqiao Xili,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bus route: take No. 300, Special Buses such as No. 8, 631, and 698 get off at Liuliqiao South Station and walk 200 meters east to the north; Exit the east-west south exit of Liuliqiao Metro Line 9, walk more than 200 meters west, and turn left through the community. Zhonghua Book Company 801 Room)
4. Readers who need to purchase online, please log in to the "Magazine Shop" website (), JD.com Zhonghua Book Company's official flagship store () and search fo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in the search bar, you can see the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follow You can purchase through the website shopping process.
5. Collective ordering phone number: 010-63458229.
6. You can also add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wszs1981" of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ime! Subscriptions are available soon, please don't miss it. If you are unable to subscribe, please remit money to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r call 010-63458229 for consultation.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