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高官巨薪难养廉为何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官员的俸禄是数一数二的优厚。《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每月俸钱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此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等,以及喂马的草料和随身差役的衣粮和伙食费。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其家属赡养费由官府财政供应。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此外,还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在京、大藩府四十顷,小藩镇三十五顷,而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
北宋实行高俸制,以养廉为目的。在北宋皇帝及其大臣心中,这一点非常明确。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 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提出了“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
然而实施效果并非决策者主观想象中的那样乐观。虽然初期有一定的收效,但很快就出现了问题。“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但贪赃恶迹仍然存在。而实际情况是良吏寡多赇取如故。此外,由于官方队伍不断膨胀,加上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重,最终导致国家经济形势严峻,即便官方提高其物质生活水平,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如何真正保证政府机构内的人才能够保持清正廉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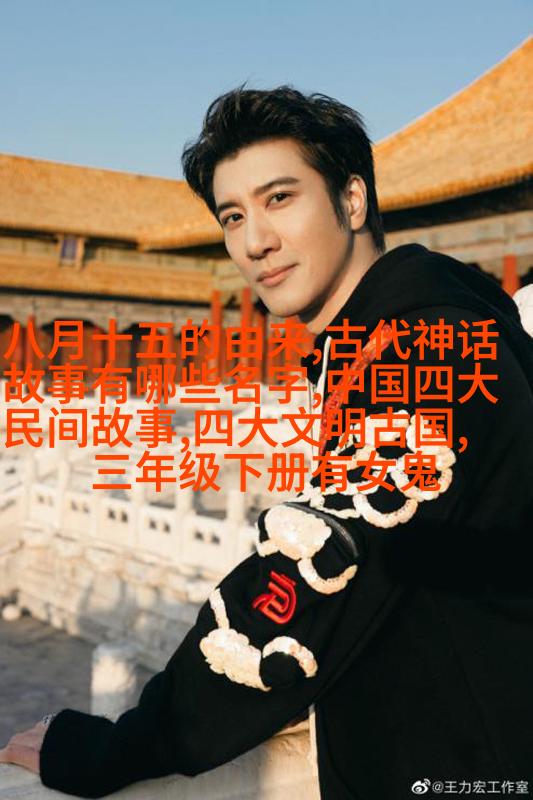
事实证明,将高额收入视作防止腐败的手段,并不能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这主要因为腐败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收入,而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标准。在相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下,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保持清正,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利用权力进行私利牟取。这意味着,即便通过增加薪水来提高生活水平,也无法保证所有的人都会变得更加清正。如果认为只有通过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才能让人们自觉遵守法律,那么这种认识显然过于简单化,对现实复杂性未能做出充分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