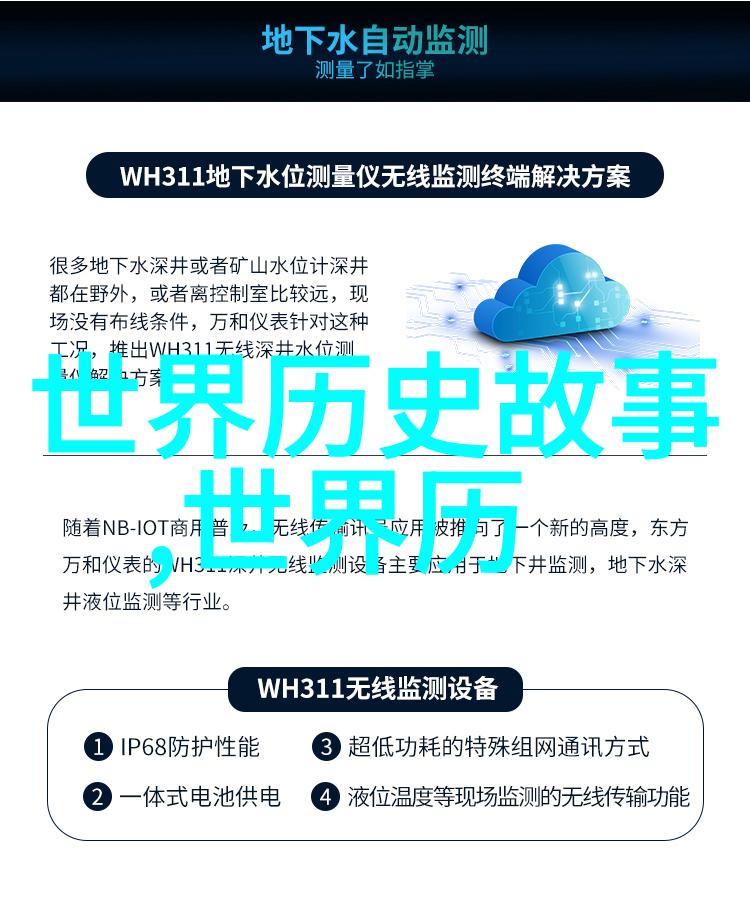包公笔下无尚方宝剑狗头铡也懵懂1988年大批神仙下凡后的包公戏以何种形式扭曲了宋朝的司法
1988年大批神仙下凡后,民间曲艺中“包公戏”的故事更是繁复多变,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与实录相去甚远。如果将“包公戏”中的尚方宝剑和狗头铡当真反映了宋代司法,那便是一场闹剧。现在,我们有必要揭开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同舟共进》2016年04期 封面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6年04期,作者:吴钩,原题:被“包公戏”扭曲的宋朝司法制度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并没有什么“包公戏”。这类故事是在元朝兴起的,而至晚清时才逐渐流行。数百年间,关于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各种艺术作品,如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以及京剧等;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改编成多部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通过这些演绎了解古代司法制度与文化;一些学者也以此为样本分析传统的人治模式,并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原因。
然而,这些民间曲艺中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与历史实际不符。如果认为“包公戏”展现的是真正的宋代 司法过程,那就难免显得荒唐。在《封神榜》中,每个神仙登场必带出自己的法宝,“包公案”的主角也携带着代表最高权力的道具,但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于那时那地的事物。

例如,在元杂剧中,只有所谓尚方宝剑,即丹书铁券;到了明清传奇,则出现了更多权力道具:“(皇帝)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其中“势剑金牌”,即所谓尚方宝剑;丹书铁券,即我们熟知的大批发:“(皇帝)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
这里提到的势剑即所谓尚方宝剑,其它则发展成为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龙头铡、大虎头铡、小狗头铡,大龙头铡专杀贵族,小虎头铡专杀官吏,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借这些令人惊叹的手段和工具,有史以来最厉害之人的形象便塑造而成——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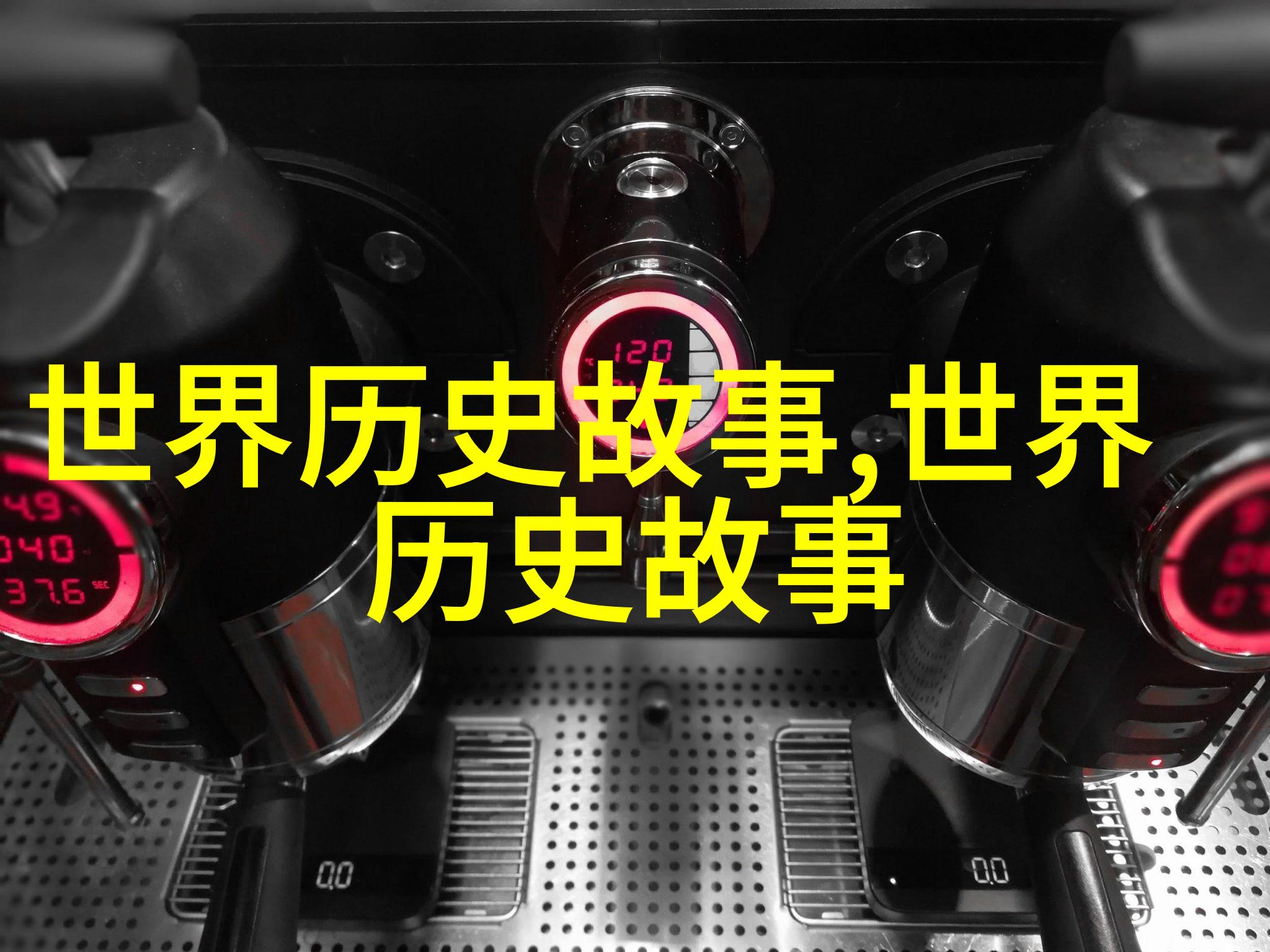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被捕者的罪犯也有类似的道具,如根据元杂剧改编而来的潮剧或川剧,都讲述世家子弟鲁斋郎,以祖传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这场好戲来了:具有最高破坏力的尚方宝剑能否打败拥有最高防御力的丹书铁券?从戏文看似乎破不了,所以最后只好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将其名讳改写,再得到核准死刑。但这种以法律为准绳分辨黑白是非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却变得愈发稀缺,而权力对决则日益增强,最终演变成了谁掌握更高级别权力道具谁胜出的游戏。
正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展示的一般,一方面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对手祭出可破黄马褂又假冒产品,这种富含幽默色彩的情节,也体现出了对传统的人治模式批判的声音。但这样的精彩纷呈的情节绝不会出现在真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里,因为在那个时候,并不存在像这样由大臣持有且可以自由使用尚方宝剣来执行超级命令的情况。而三口金属刀,更像是民间文人幻想后的产物,从未见于历代行刑记录之中,不可能真的作为刑罚之一设立。此乃后来随着蒙古人的影响进入民间文学作品,并逐渐融入到每位读者心中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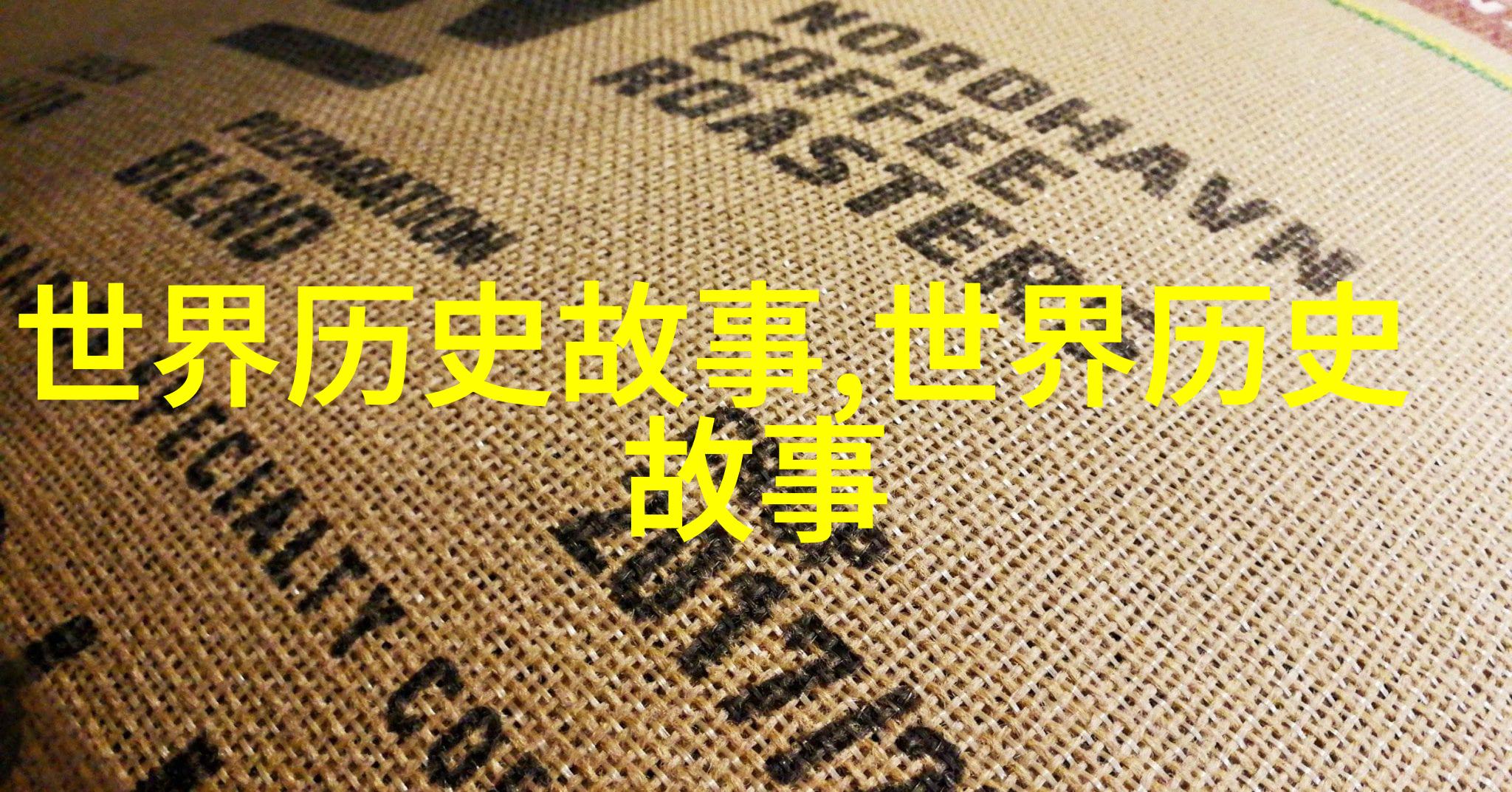
因此,如果要深入理解和认识真正意义上的古代中国法律体系,就必须抛弃那些充满奇幻元素与夸张描写的地步,让历史回到它应有的轨迹上来。